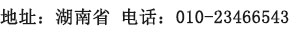//-02-03//
有
爱
就
有
阳
光
灿
烂
文菈妈
这世上最扎心的事,莫过于:
「我不要长得像爸爸……呜呜呜……」
一个4岁的小萌娃,正吃着蛋糕,突然听到别人说她长得像爸爸,手里的蛋糕,顿时就不香了,嚎啕大哭,死活要跟爸爸「划清界限」。
她一边抽噎着擦眼泪,一边还不忘表白妈妈:「我想长得像妈妈。」
如果硬要给对妈妈的偏心找一个理由的话,那就是——「爸爸太丑了!」
孩子泣不成声地「甩锅」,让不少网友笑翻了,纷纷调侃:
「说好的小棉袄,怎么漏风了?」
「爸爸该哭晕在厕所了……」
哈哈哈!心疼这位爸爸一秒钟。
不要问孩子为什么只爱妈妈,也不要试图了解「真相」,因为你很有可能承受不住这样的暴击。
毕竟,喜欢就是喜欢。但不喜欢,总能找出一万种不喜欢的理由。妈妈的好,爸爸怎能比得了
同样嫌弃爸爸的,还有这位4岁的小男孩。
妈妈感冒了,让儿子去跟爸爸睡,没想到儿子死活不同意,又哭又闹,外加彩虹屁:「我的妈妈最漂亮了!」
把妈妈捧上天之后,还不忘回踩一下爸爸:「爸爸太丑了。」
可是,妈妈明明吐槽儿子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啊。
孩子呀,这理由,未免太牵强了点吧。
除了长相被攻击之外,在孩子的心里,爸爸的爱也被妈妈「秒成了渣」……
一位爸爸,因为女儿写了篇作文,全篇都只歌颂妈妈的爱,半个字都没有提到自己,气到变形,嘶吼道:
「衣服谁买的?牛奶谁买的?房子谁买的?」
「是妈妈一个人赚钱养家吗?」
没想到女儿斩钉截铁地回答:「都是妈妈买的,爸爸没有爱。」
爸爸怒了:「爸爸没有爱?你今天必须强行写出来,爸爸的爱在哪里!」
真是嫉妒让人面目全非啊,隔着屏幕都能听到爸爸心碎的声音。
这可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只照妈。
孩子偏心起来,那可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哇!
当然了,在孩子心里,爸爸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这个小萌娃,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第一时间想到了爸爸。
「妈妈,你不要去上班。」
一个4岁的小男孩,眼泪汪汪地乞求妈妈。
当妈妈问,自己不上班那谁去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让爸爸去,爸爸可以工作赚钱养你!」
为了让妈妈相信自己的真诚,他还眼含热泪、拍着胸脯说:「我的心跟妈妈在一起。」
有这样的萌娃,估计妈妈的心都要甜化了。
妈妈有多甜,爸爸就有多惨,真正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孩子偏心,只因爸爸太不靠谱
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不要抱怨孩子偏心,要知道:爸爸们可是凭实力,被孩子嫌弃的。
先来看看一些爸爸带娃都有多不靠谱:
爸爸带娃,果然是活着就好。孩子这是冒着生命危险,陪爸爸看海浪。
就连检查作业,也是心不在焉。
妈妈带娃尽心尽力,爸爸带娃野得不行,就这态度,如何能与妈妈争宠?
如果你自问并没有不靠谱,那很有可能是因为「粑粑」,影响了你在孩子心中的高大形象。
「为什么你们跟妈妈比较亲呢?」
上一秒还一脸平静的姐姐,立马义愤填膺地回怼:「因为你不是在拉粑粑,就是在拉粑粑的路上。」
怼完还不忘温柔地对弟弟说:「你以后不要像爸爸那样,知道了吗?」
这位爸爸,不要再和「粑粑」没完没了了好吗?你那点小九九,就快要藏不住啦。
这年头,爸爸们不光不靠谱,还让孩子操碎了心。
一提到爸爸,儿子的吐槽就一波接一波:懒虫、不讲卫生、不爱洗澡……
最后,还不忘发出一声哀叹:「我长大都想好好地收拾他一顿!」
这挑战,爸比,你接收到了吗?
除了各种不靠谱之外,横在爸爸和孩子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手机了:
「我爸爸特别喜欢看手机。」
「我爸爸三更半夜还躲在枕头底下玩游戏……」
不陪孩子玩,还想孩子跟你亲,怕是只有做梦才能实现了。
当然,也不乏有些爸爸是为了撑起这个家,默默扛下了所有,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拳王邹市明曾说,因为缺席了儿子轩轩的成长,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儿子都只冲着国旗、冲着金牌喊爸爸。
事业与家庭,工作与陪伴,注定无法完美平衡,这才是最扎心的现实。
付出多少爱,才能收获多少亲密
可扎心归扎心,这都不是借口。
心理学家格尔迪曾说:「父亲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因为爸爸身上男性独有的勇敢、坚韧、乐观等特点,恰好能与妈妈互补。
也许,你会困惑于该如何当好一个爸爸。但反过来想一想,自己小时候最希望爸爸为自己做什么,就了然了。
一个父亲,对孩子最好的爱,莫过于陪他一起玩。
有一位父亲,用废旧的纸箱,给女儿做了件玩具,有俄罗斯方块、塔吊、极品飞车等等。
构思之巧妙、做工之细致,让不少网友叹为观止,更别提玩得不亦乐乎的女儿了。
曾经感慨想要息影、当个全职爸爸的邓超,常常忙到脚不沾地。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飞回去陪孩子。
他会给孩子讲一个多小时的睡前故事,哪怕自己中途累到睡着了好几次;
一有时间就下厨,给孩子做好吃的;
一张纸、一个木偶,也能陪着孩子玩出许多花样来……
他最大的骄傲就是:「我多好玩呀,我是孩子最大的玩具。」
再忙,也不妨碍用心的爸爸,把有限的时间,变成高质量的陪伴。
《奇葩说》里主持人问孩子,最爱的玩具和爸爸的陪伴,他们会选择哪一个,所有的孩子都选择了要爸爸陪伴。
有一个男孩还很贴心地选了一个足球玩具,因为「爸爸喜欢踢足球」。
可见,吐槽归吐槽,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为爸爸留了「一席之地」,渴望能和爸爸一起愉快地玩耍。
爸爸,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而是付出了爱和精力,才成了孩子心中的「爸爸」啊!
画家刘墉曾经说:
许多爸爸在孩子的图画里,没有手。
因为在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像一团影子,总是抓不住。
或许你有太多的事要忙,工作、出差连轴转;
或许你也有委屈,孩子总是粘妈妈、不粘你;
或许你的爱一点也不比妈妈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可孩子的成长不可逆,错过了就回不来了。
如果你不想再被孩子「冷藏」,不妨从现在起,用心陪伴、用爱相守。
毕竟,付出多少爱,才能收获多少亲密!
-END-
试卷上就
在我幼年时,参加大人们的饭局,可以在我最讨厌的十件事上排到前三,与老鼠和香菜匹敌。
中国人有句古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于是我就成了那头骡子,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拉出去溜。遇到心心相惜的骡子,还算幸运,两相承让,合作共赢。可遇到一眼相望就能掀起战火的,虽是同类,还要以仇敌待之。
我人生遇到的头一个骡子是小伍。小时候她身体弱,爸妈给她起了个男孩的小名,说好养活。我喊小伍妈康阿姨,她和我妈同龄,十八岁时两人进了同一个厂子工作,住同一个宿舍,就差没睡同一张床。打从我俩光着屁股起,就被大人们送上了斗兽场。
吃饭结束后的午休时分,厂里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
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
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你先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
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来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的其他阿姨争相来到宿舍,把我俩放在同一张床上,开始比较我们谁的眼睛更大、鼻梁更高、嘴巴更小,连谁哭得少都不放过。
长大一些,我们需要当众表演一场抓周,看谁以后更有出息。可能因为在一张床上抱团滚了不少次,我俩还算相互体谅,谁也没比谁出众,小伍抓了支眉笔,我抓了本书,正当众人笑谈之际,只听“哗啦”一声,书被我撕了。
打我和小伍开头,厂里的许多孩子,此后都过上时不时就要走上斗兽场的紧张生涯。
和我妈一同进场的大约有二十个阿姨,其中有十位关系最亲。从厂里出来后,她们保持了友谊,也保持了随时聚会随时竞争的良好传统。
这些阿姨的孩子们,有两位姐姐比我和小伍大好几岁,没参与当年那场竞赛。但大人也没放过他们,一有聚会,必带她们出来。
大点的姐姐学跳舞,小点的学手风琴。聚会饭后之余,在父母的推搡间,她们免不了要表演一段。跳舞的姐姐在节奏欢快的音乐里转动,脸上却愁云惨淡;学琴的姐姐不好把手风琴背到饭局上,大人们一致决议:唱首歌吧,都是音乐嘛。她为难地说自己五音不全。长辈们都笑:怎么可能呢?姐姐迫不得已唱上一首,观众表情一言难尽。
我十分疑惑,连我一个小孩都看得出来,姐姐们不高兴表演,难不成大人们看不出来?
但我和小伍曾经很羡慕她们。因为后来她们很少参加饭局,一句“课业多”就能打发许多事。即便要来,也只是吃个饭,随后背着书包匆匆离去。
毕竟等她们从斗兽场退出后,我和小伍就要开始打头阵。
小时候我俩都学舞蹈,但分别在不同的舞蹈学校。这给了大人们一个极好的理由,“赶紧一人来一段啊,看哪个学校教得好”。
我和小伍互相推诿。“你先来。”“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
“不,还是你先。”
不知哪位阿姨从后面顺手推一下,其中一个人先出去了。有时是我,有时是小伍。我们俩学的都是民族舞,表演民族舞时最典型的表情是笑,不笑简直都不会跳了。
我和小伍毕竟还没修练成昔日那个大姐姐,能神色悲切地跳下去。小伍跳的是孔雀舞,我跳的是红色娘子军,这没法不笑着跳,只好咧着嘴跳完舞。大家于是都觉得我们在这种场合十分欢快,乐于表演。
作者图
穿着舞蹈服在水边留影
后来我学了手风琴,小伍学电子琴,再后来我俩都学了钢琴,我在心里庆幸:没工具,怎么比?但好景不长,我们的竞技场升级了。
那几年,各家都从大杂院搬进楼房,聚会从透风的老饭馆换到自家。过年时最热闹,十一家轮流做东,每家一天。
轮到我家或小伍家时,是我们最煎熬的时候。我们的钢琴房成了二十来个人的围观场所,大人们的要求也更多了,要弹两首以上的曲子,不能看谱,实在弹不下去才能看。不过看了谱子,胜负也就区分出来了。
小伍和我身经百战,早就结成同盟。我俩的对策是,两人都看谱,弹的曲目十分接近,外行很难听出来什么,最后观众只得念着“两个都很好”的台词散场,看上去十分失望,有种一定要比较出什么的执着。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和小伍般默契,我们很快碰到了搅局的人。
二
来搅局的女孩比我们小三岁,她叫彤彤。
彤彤同我们并不算亲近。一来,之前她不怎么参加饭局;二来,从见到她的第一次,她就表现出一种势必一较高下的气质,这常会吓到我们。
在我和小伍走上斗兽场的那几年,她正在家中勤学苦练。她母上李阿姨对她要求极为严格,技艺不练到最好,轻易不拿出手。
要论这点,我妈和康阿姨都只能甘拜下风。
因为我和小伍都学舞蹈,李阿姨给彤彤也报了舞蹈班。我们在同一个学校,但接触极少,我入学早,已在大班,她还在小班。
有几次,我试图在中场休息时同她讲话,但她的头昂得如天鹅一般,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仿佛随时准备释放一个开打的信号弹。
我的表现也由此不善。因为是大班里年级最小的女孩,我一直是老师的宠儿,有天我连翻了二十个前滚翻,老师抱起我,将我顶在肩头以示鼓励。我兴高采烈地大叫起来,目光有意识地寻找到彤彤,不出所料,只见她也正望着我,神色莫辨,几乎是不自觉地,我朝她笑了一下。
我看不见自己的表情,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坏人的笑。因为当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西游记》里蝎子精的样子。
我没再盯着彤彤看,也不清楚她后来做了什么,我还不是那么善于消化战火的小孩。
那天后没多久,她退了班,再见面时,她拉上了手风琴。等她拉上手风琴没多久,我和小伍开始学钢琴。照此发展下去,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竞争关系。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
彤彤第一次在她家组织的饭局中表演节目,当时她上四年级,我和小伍都是是初中生了。彤彤的手风琴功底了得,可谓厚积薄发,弹琴时手指灵活,节奏稳当,仪容到位,时而侧耳,时而闭眼,以她幼小的身姿,竟然还能拉出一股款款深情来。
在座的当下都是一惊,随即真诚地鼓起掌来,李阿姨的脸上闪现出神女般的光彩,整晚不去。彤彤连弹三首,在众人的掌声中颔首微笑,像极了一个优雅体面的大人。
五年级时,她拿了一个挺有分量的奖。这在姐妹圈中涟漪四射,彤彤顿时成了优秀的别人家小孩,我和小伍每天至少得听三遍她的名字。
当我们再长大一些,又有了其他可以比较的项目。尤其是上了中学后,谁长得更高、谁成绩更好,连谁更会看眼色也加入比较大潮。
彤彤父亲一米九,母亲一米七六,她基因强大,身高直接秒杀我和小伍。
在成绩上,上高一时,我和小伍分到了一个班,还做了同桌,每天上课除了睡觉就是聊天,成绩一落千丈,还因为经常迟到在全校家长大会上被通报批评,我妈和康阿姨常常是全程黑着脸走出学校。
而彤彤那里却总是能听到好消息,比如考试又进入全级前十名,手风琴又拿了什么奖。
在眼力方面,我们更是甘拜下风。聚会时,她相当懂事地给所有人泡茶。把从家里自带的茶叶倒入壶中轻轻摇晃,茶叶浸泡的淡黄色立刻晕染开来。泡好茶叶后,她端着茶壶从坐在上客方位的叔叔开始,顺着往下给每个人添茶。添茶时,彤彤的身体立得笔直,俯身时也相当得体。每添一杯茶,座位上的长辈就向她道谢,溢美之情溢于言表。而彤彤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收回端着茶杯的胳膊,以免碰撞到杯子或餐具。
这还不够,她总能第一个注意到谁的茶杯空了,谁缺了副餐具,还会主动喊服务员要菜谱。一整套流程行云流水,无可挑剔。我惊叹也许她从一出生就属于成人世界,身上看不到一丝任性,仿佛从来没有过孩童的时候。
因为彤彤的完美,我和小伍成了被挂在饭席上的批判对象。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要向彤彤学习。
因为这,李阿姨一度是饭局上最神采奕奕的人,无论是不是她请客,都前前后后地张罗着,步伐轻快。康阿姨和我妈有时就有些难堪,主要是我和小伍脸上的表情不太给面子。
彤彤坐在李阿姨的一旁,身姿挺拔,两手乖巧地放在餐桌上,接受夸奖。有时她像是害羞地说:“姐姐们也很好。”她看向我,双目相对,彼此很快移开,大抵都从对方脸上看出来俩字:虚假。
越是在此时,我和小伍越是昂首挺胸。这个姿态的意义在于:虽然你赢得了长辈的赞美,但我们对此毫不在意。我和小伍从饭局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无法在某一个维度上打败敌人,那么你就假装高出这个维度。
因此,我们总是在表情上做出与年龄不符的超脱,这一度给长辈造成不好的印象。毕竟我们极其幼稚的面孔,表现出的只能是孩子的骄纵。
我妈从小不吝惜棍棒教育,现在教育我时更下狠手。她和姐妹们的普遍认知是,孩子可以粗心调皮,但绝不能骄纵。骄纵意味着挑战权威,破坏长辈管理权的合法性。
我越是不乖,我妈越认为需要多拉我出去溜溜,多方位杀杀我的锐气。饭局,成了我逃不出去的困局。
三
彤彤在和孩子们的比较中大获全胜后,我和小伍主动和她划开界限,主要原因是彤彤似乎十分情愿来到饭局中。
在我们极其幼小的时候,就被迫成了一只骡子,我们还来不及思考为什么,已经被拉出去溜了一圈又一圈。如果有骡子十分情愿出去溜,那一定不是我们的同类,她也许是匹马。
我和小伍对彤彤有了些温柔的情绪,是从小伍目睹了彤彤在家的糟糕经历开始的。
当时康阿姨出差,将小伍寄放彤彤家。那是个周末,彤彤早上六点被喊醒去做功课,小伍睡得稀里糊涂,只听见李阿姨训斥说:“几点了,还不去写作业?”
等到小伍起床时,彤彤早已做完了功课,要开始练琴了,那时是十一点半,距离中午饭只剩半小时。在我和小伍的概念里,此时已经到了放松的时候,既不够时间去练琴,功课也完成得差不多,我们应该看会电视,然后等待开饭。
但李阿姨不愿放过每一个零碎的时刻,大概是起来太早,彤彤练起琴来很没精神,她想要下午再练。因为这件事,李阿姨拿起扫把,在彤彤身上抡了一下又一下。小伍回忆说,这比她在我家看到我挨打更惊恐。她想上前劝说两句,到底没敢,又不好意思走开,最终缩在墙角,被迫观看了一场暴力电影。
小伍总结说,我妈打我,胜在数量,李阿姨打彤彤,则胜在质量。那个场景给她留下极深的阴影,此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李阿姨家。
那天回来后,她跟我在电话里说,原来彤彤不是马。我也心有戚戚焉,目睹了彤彤的失败后,我们在电话两端都有些低落,想到我们身为骡子的共同命运。
再一次见到彤彤时,她有些不好意思,显然不像之前那样傲慢。我们主动凑过去跟她说话,提到上次李阿姨揍她时,她扭过头去,我很厚脸皮地凑上去说:”这没什么,谁家孩子还不挨揍呢?”
整个饭局都沉默起来。彤彤看了一眼李阿姨,连添茶倒水也顾不上了。李阿姨喊了几声,她都好像没有听到。李阿姨顿时没有了以往的神采,她批评彤彤不懂事,其他阿姨赶紧出来打圆场:“孩子嘛,不要这么苛刻,咱们自己倒。”
她们反倒比李阿姨更精神奕奕起来。
在阿姨们的饭局中,我曾数次看到这样的反差。
当我们这些小孩在展示自我的过程中不那么成功,或出了差错,饭局的氛围反倒会欢天喜地一些。当然,除了自己的妈妈。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察觉到这种奇怪的氛围,并对此不解。在我看来,这些阿姨亲如一家,她们几乎是看着我们长大的。
一次在我家,长辈们让我拉我许久没有碰过的手风琴。我推辞说,肯定拉不好,手生了。我妈也跟着推辞,但是阿姨们意见一致,想看我拉一首,“随便拉一首就行,拉错了我们也不会笑话你”。
当我吭吭哧哧拉完一首时,我妈的脸色果然十分难堪,李阿姨笑着说:“才多久没练就忘了啊。”她严肃的脸上露出极少出现的放松,其他阿姨也附和着,李阿姨旁边一位阿姨看了一眼我妈,用手轻轻推了李阿姨一下,李阿姨咳了一声,用宽和的声音对我说:“没事,继续努力。”
李阿姨不止一次地要求我弹奏许久不练的曲子,在出现错误之后,又延续她宽和的安慰。
我无法抑制恶意地认为,那种宽和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仿佛我是一个演砸了的小丑演员,凄惨退场只为了给她的女儿腾出舞台。
四
大多时候,比较还会从外面延续到自己家里,我和小伍开始顽抗自己被溜的命运。
小伍不乖时,康阿姨惩罚的方式是冷暴力,康阿姨既不和她说话,也不正眼瞧她,也不允许家里其他人跟她说话,有时候她在家中透明人一样度过一周。
你要以为小伍会反省、会自我痛苦,那就大错特错了。起初,她开心得不得了,再没人唠叨她了,但小伍的妹妹诞生以后,事情变得复杂。大约是小伍上五年级,就要到了叛逆的时候,只要小伍不合作,康阿姨会对她妹妹极尽可能地好,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对小伍毫不理会。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小伍很快被迫向康阿姨服软,接受一切不平等契约,包括去阿姨们的饭局。她妹妹在极小的时候仿佛已经看懂这一切,非常配合母亲,并乐于向姐姐炫耀自己的战利品。
剩下最后一个大题了,醒目的空白
第1章林中阴谋
耀日国
云月城
青山叠叠与云雾相缠绕着,山林中茂盛树木在轻风中摇曳,这晨起的山林显得是那样的清幽雅静……
然,就在这偏僻无人的山林深处,此时却上演着残忍而血腥的一幕。
一名穿着上等绸缎的少女此时被两名精壮的汉子反扭着手臂按跪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垂低着脑袋,凌乱的发丝垂落脸颊却很快的被脸上渗出的鲜血浸湿,鲜血一滴滴的垂滴落地面,渗入泥土。
气息极弱的少女在听到脚步声走近时,咬着牙抬起头来,露出了一张血迹斑斑的脸,那是一张被毁了容的脸,脸上的皮肤生生的被刀刃划开,血肉模糊,十分骇人。
“你是谁?为什么要害我?”少女的声音极弱,有气无力的传出,强撑着因失血过多而产生的昏厥紧紧盯着那用轻纱遮着脸,身段极为优美的女子。
那看不见容颜的女子一袭淡蓝色水云裙子着身,腰间同色的流苏垂落着,随着她轻盈的步伐而轻轻摆动煞是好看。
她在那被按跪在地上的少女面前停下脚步,居高临下的睨着此时容颜被废的少女,带笑的美眸弯弯的说道:“我是凤清歌,护国公府的大小姐,威武大将军凤萧的掌上明珠,凤家卫的少主,凤家未来的继承人,同时,还是耀日国的天之骄子三王爷的未婚妻。”
熟悉的声音以及面前女子所说的话,让少女震惊的睁大了眼睛:“你!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才是凤清歌!我才是凤清歌!”纤弱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形成,眼中溢出了无法置信。
白皙纤细的手指轻轻一揭,遮着容颜的面纱轻轻落下,一张绝美中带着清雅的容颜便这样映入地上少女的眼里,当看到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容颜时,她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绝美的容颜轻仰,睨着地上面容骇人的少女,她的声音带着无限的期待与难抑的兴奋:“凤清歌,从今天起我将取代你的身份,你的位置,理所当然的拥有你的所有一切,而你……”声音一顿,她低笑着:“以你的聪慧,不如想想我会怎么对付你?”
听着眼前之人那原本的声音传出,凤清歌身体一颤,无法置信的睁大眼睛看着她:“若、若云?你、你是苏若云!”
苏若云,一个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孤儿,是她把大街上的她带回了护国公府,是她把她留在身边相依为伴,是她无话不谈的闺中蜜友,是她视为亲人的姐妹……
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毁了她的容颜之人,想要夺取她身份地位的人,竟然是她……
“为什么?我待你那样的好,为什么你要这么做?”被背叛的心如刀割般痛,想到自己的容颜被毁,身份将被取代,而这将无人能知,恨意不由袭上心头。
“为什么?呵,当然是为了你所拥有的一切,视你如珠的爷爷和父亲,爱你入骨的天之骄子,不过……”她美眸弯弯一笑的看着地上的凤清歌:“这一切,都将是我的了,爷爷和父亲的疼爱与宠溺,慕容哥哥的温柔与深情,都将是我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