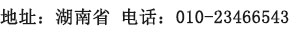原创作者:褚邹嫄同济大学
责任编辑:耿倪帅同济大学
本号编辑:马万祺华东政法大学
公益平台:文化上市公司
WXID:CulturalCompanies
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当下科技语境下的一个重要话题,人机混合的产物——“赛博格”成为了后人类形态的隐喻。科幻电影中拟人化赛博格形象的物质性身体的建构,体现了人类对自身身体的困惑所在。人们诉诸于赛博格身体的塑造,是自身造物情结和义肢幻想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借此寻求自身身体转变的投射,开启了一部全新的人与机器关系的历史。
一、科幻电影中赛博格经典形象划分
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中提出,赛博格身体的特质在于打破界限,然而问题在于界限的临界点在哪里?在大众的共识中,大多还是以人作为赛博格身体的最终目的,即无论创造物被植入了怎样的机械体或非物质成分,其中人类的部分依然是我们认定的核心。不可忽视的是对赛博格身体模糊性的隐忧,这一点在影视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或可将其视为电影创造者对现实生活的引申,通过梳理科幻电影中赛博格形象的流变,来观察身体作为赛博格存在的媒介如何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从而畅想后人类纪的世界存在。
《机械战警》(RoboCop,)塑造了一个有着人类头脑和机械身体的机械警察墨菲。他的赛博格身体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穿着盔甲的人而不是除人脑以外完全由钢铁拼接而成的机械身体。但在电影中呈现出来的不自然的肢体动作以及出场时特有的机械响声,导演力求打造的是一具明显异化的机械身体在其人脑的支配下打击罪恶,寻找家人,展露出充满人性的一面。《星球大战》(StarWars,)中的黑武士达斯·维达同样是通过机械体植入来改造身体。他特有的呼吸声和沉重缓慢的脚步声往往是人未到声先至,这一点上与机械战警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黑武士作为《星球大战》中的反派,他非人的特质在片中是以制造恐怖的目的呈现的。以上两部电影所塑造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以机械体植入的方式改造身体的经典例子。另一种通过改造人类原始身体形成赛博格身体的类型是基因改造。这一类型的出现与基因技术在现实生活的发现与应用有关,是哈拉维所说的人类与动物的界限被突破的反映。《异形》(Alien,)、《X战警》(X-Men,)、《美国队长》(CaptainAmerica,)中创造了为人们所熟知的基因改造赛博格形象。《异形》中采用的是寄生的方式,《X战警》参考电影设定来说变种人的产生更偏向基因突变,从《美国队长》的影片可以看出是基于化学注射的基因改造使得瘦弱的罗杰斯变成了十倍于普通人类极限的美国队长。总的来说,以上所列举的赛博格形象,其关键的生命器官是人类的器官,属于狭义赛博格定义“机械化有机体”的范畴之中。这之中由于机械体和技术因素的介入,身体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对身心二元的探讨也是身体改造影片中所常见的核心问题,但其中的赛博格形象却往往是温情脉脉的。在这里,赛博格身体向动物、机器的一端游移,观者对其的情感认同,或者说银幕形象所呈现出的情感倾向却偏向了人性的一端。
《攻壳机动队》(GhostIntheShell,)所呈现的是更复杂的机械化有机体形象。“若吾起舞时,丽人亦沉醉。若吾起舞时,皓月亦鸣響。神降合婚夜,破晓虎鸫啼,远神惠赐。”影片开头响起名为义体人降生(IMakingofaCyborg)的谣词,与此同时画面上是一具人体形状的机械体与肌肉组织的结合体包裹着人脑组织,其外连接着无数流水般的悬丝,整具身体在液体之中诞生,仿若婴儿从母亲的羊水中诞生。但与其说是诞生,不如说这一系列过程是实验室中精密的装配操作。最后,义体人身体之上附着的硬质慢慢在液体中剥落,其下隐藏的鲜活的女性肉体渐渐显露,草薙素子由此生成。草薙素子的身体之所以特殊,是由于构成她“人”的一面的脑组织寄居在机械金属的外壳中,这一部分器官能否被定义为维持生命的关键器官是暧昧的。当我们谈论身体时,作为肉眼无法看见的器官,人脑总是被间接地联系起来的。这也是素子对自身产生主体怀疑的根据所在。而随后在剧情中出现的傀儡师,作为一个在网络信息的洪流中产生生命的意识个体则,本身不具有身体,而是通过网络侵袭和利用他人身体。相比于《机械战警》和《星球大战》中较为坦白的机械化身体的变形,《攻壳机动队》中多样的身体变化和身体结合方式创造了“机械化有机体”更多层次的身体内涵。
二、赛博格身体的起源与构成
(一)赛博格身体的起源
赛博格这一概念在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但它的形象从产生到现在却有着数千年的时间跨度。从希腊神话中的喀迈拉到东方神话中的孙悟空,其异质混合体的本质始终没有发生改变。而当唐娜·哈拉维呼唤出“我们都是喀迈拉”时,赛博格的定位就已经发生了转变。
在哈拉维看来,赛博格身体旨在打破人与自然的边界,如何界定身体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作用。简而言之,我们的身体是否是赛博格,哈拉维认为,只与我们如何看待身体有关。因此,当她想要打破父权制身体观念时,她大胆宣称我们的身体就是赛博格身体。可以说,赛博格的身体焦虑大多正是来自自然身体与社会身体的不可调和。
(二)赛博格身体的构成
拟人化赛博格的出场,正是诠释人类身体与赛博格异质身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最佳例证。脸和躯体决定了什么样的身体会被我们认为是类人的,在类人的身体中,机器、技术手段等异质的介入对身体进行的解构,更能使得观众明晰对模糊的身体界限这一点的反思。而《银翼杀手》和《攻壳机动队》正是从两个侧面反映了赛博格身体所体现的身体界限问题。
1.脸
当人出现在影像中,人脸就会成为当前那一帧图像的中心。而当拟人化的赛博格出现时,人们则会被其跟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相似的脸庞所吸引。正因为拥有脸,赛博格才有了与人类交流和互动的可能性。脸是赛博格身体的完整性和深度的保证。
《银翼杀手》中作为移情测试被测试者的瑞秋,出场时其精致的妆容与发型呈现了一种距离感的美,此时她的目光是冰冷而不带感情的,微笑的表情也只是嘴角的上挑。在移情测试之后她也被证实是被植入了记忆的复制人。根据复制人制造公司的创始人所言,记忆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情感的体验,从而更容易操控。随后已经知晓自己复制人身份的瑞秋在另一个复制人手下救下了银翼杀手德卡,在这里,瑞秋的情感倾向是明显偏向人类的。因此,在德卡公寓中的她散下梳理整齐的头发,柔和的打光使她的目光与脸部呈现“人”的色彩。面具化的赛博身体开始向人性的一端靠近。
而另一位女性复制人角色普利斯的妆容和发型相比瑞秋要显得更加僵硬和怪异,过于蓬松的发型和假面般的脸部妆效加上夸张的脸部表情,仿佛是一个做工失败的娃娃。如果说观众第一眼看到瑞秋并不能分辨出她的非人身份,那么普利斯的身份则是不用剧情特意说明就能从画面中感知。随后她来到塞巴斯蒂安的工作室中,用其给娃娃使用的油彩涂抹在脸上和眼眶周围时,过度物化的妆容使她的赛博身体从伪装的人类身体变为双重异化的他者形象。而在她与德卡搏斗时,脸上显露出的狰狞表情又显露出她拟人化身体之下的非人本质。最后她连中数枪,倒在地上死去的时候,所袒露出来的血肉模糊的伤口使她看上去仿佛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普利斯的赛博格身体经历了由人到物的变形过程,与瑞秋在观者眼中由物到人的变化相比,两具相同功能型号的赛博格身体的命运迥异,产生差异的是两者之间社会化性征的表现。在电影画面能指之下,我们看到的是社会身体产生的情感对于自然身体的催发作用。无论是因为被植入的记忆,还是因为经历对人类产生情感的复制人瑞秋可以成为女神,而被迫成为弑杀机器的赛博格则只能成为脱离躯壳的幽灵游离在世界之外。
尽管似人的五官面容和传情达意的目光给予赛博格传递人性的可能,但其身体中属于人工的那部分始终如影随形。《银翼杀手》中用以判断受测者是否是复制人的移情测试,通过机器检测受测者在回答相关问题时产生的“脸红反应的微血管扩张”、“瞳孔的波动”、“虹膜不自觉地扩大”,从而判断其是否具有人类特有的移情能力。这一测试是《银翼杀手》原著作者根据图灵测试所虚构的产物。图灵测试是指,当测试者向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随意提问,而在多次提问之后无法分辨人与机器,就认为这台机器通过了测试,拥有人类智能。《银翼杀手》中哪怕是被植入记忆的复制人瑞秋也没有通过这一移情测试,而《机械姬》中通过说谎、色诱、杀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伊娃却通过了这一测验。值得反思的是,科幻电影中刻画的“更像人”的赛博格是否只是人类的神化?承载着赛博格身体非功能性的脸的背后,赛博格的“自我”意识若隐若现。
2.四肢躯体
如果脸是承载着表情情感的身体部分,四肢躯体就是赛博格身体功能性的体现。在科幻电影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对于赛博格身体的建构偏向人们心中对完美的自然身体的想象。四肢躯干是身体力量感的象征,因此影片往往塑造拥有健硕肌肉的男性和矫健身姿的女性身体。赛博格身体的“被制造”和“可置换性”是保证其四肢躯体运作良好的保证。
《攻壳机动队》的公安九处几乎人人都配备义体组织用以增强自身机能,一旦在战斗中身体受到损伤还可以修补和置换。《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在制造时就以不同功能分类了不同型号。从这一层面来看,赛博身体的的四肢躯体直指对身体的物化倾向,身体的功能性成为改造身体的最终目的。对自然身体的刻画曾经是浪漫主义乡愁的产物,而赛博格身体的可置换性和特殊功能性摧毁了身体边界的确定性,从而踏入了后人类的纪元。
图1
三、赛博身体的隐喻
(一)赛博格身体的双重矛盾性
保罗·利科在《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的最内在和最高的地位……是‘是’这个系动词。隐喻的‘是’既表示‘不是’又表示‘像’。”赛博格正是从身体的“不是”与“像”之中确立了人与异质物的隐喻关系。人的身体与机器和技术构造的异质身体共同构成了赛博格身体,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说人是机器,但人与机器之间又存在天壤之别,正是介于“像”与“不是”之间的这一内在双重矛盾的关系被概括进了赛博格这一隐喻物之中。而我们借助科幻电影这一媒介,放大业已存在人类身体中的异质成分,以此提醒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