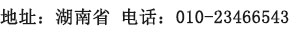阿兹夫定作为首个国产新冠口服药上市时公布的新冠临床试验信息非常少,从药企8月寻求IPO时公布的部分材料看,这个药物的有效性极为可疑(阿兹夫定有效性可疑)。
除了信息透明度低,有效性极为可疑外,这个药真正让我觉得在新冠治疗上一棍子打死也不冤的是,它潜在的遗传毒性(致人体基因组突变)与生殖毒性问题。这些问题有理由让我们怀疑阿兹夫定是否应被允许用于新冠治疗,至少它不能成为首选药物。
1.体外体内遗传毒性均为阳性
阿兹夫定在年7月根据一个二期非劣性试验获批用于HIV治疗,也多亏一年前的这个批准,我们能找到当时药品监管机构的技术评审报告[1]。
该报告提到阿兹夫定在遗传毒性实验里,“本品Ames试验、CHL染色体畸变试验和体内小鼠微核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遗传毒性(genotoxicity)是某个化学物质导致细胞内遗传物质发生突变的能力。对于一个药物,我们需要评估遗传毒性,因为万一它能导致人体细胞的基因组发生突变,那就有潜在的致癌性、致畸性等严重安全问题需要考虑。
遗传毒性不是一刀切的风险。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评估遗传毒性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用实验室培养的细胞,看看药品有没有在这些培养的细胞里导致突变,也可以在动物实验里观察有没有突变发生。同一个药物用不同实验,做出来的结果可能不一样,我们只能综合考虑,给出一个风险上的评价。
从不同检测方法的结果来看,阿兹夫定的评审报告包括了三种常用的遗传毒性评估方法:Ames是用细菌分析致突变性,CHL染色体畸形用小鼠细胞观察,体内小鼠微核试验是在动物身上直接研究。三者与人体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递进关系,细菌是原核生物,与人体细胞相差甚远,小鼠细胞就接近很多,但体外培养细胞与真实的药物使用还是有很大差异,到小鼠体内试验,基本是遗传毒性在实验阶段能与人最接近的情况了。
这三个全部是阳性,也就是都能观察到阿兹夫定的致基因组突变现象,遗传毒性可以说是不容忽视。
遗传毒性还要在另一个层面考虑,那就是药品的风险收益。如果是不治之症,那对药物的毒性标准,包括遗传毒性的风险耐受度会更高,或者说更宽容。如果没有其它药物可替代,那也不得不宽容。
到阿兹夫定的新冠治疗上,遗传毒性无论在哪个层面好像都不该宽容。参考同样遇到潜在致突变风险的默克口服药(molnupiravir)。在FDA上市审核时,遗传毒性成了这个药重点讨论的话题。实际上多种实验里,molnupiravir只有一个Ames实验阳性[2]:
与实际药物使用更接近的动物体内实验都是阴性,即便如此,FDA仍然对默克口服药做出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孕妇与未成年人直接排除在外,剩下的也必须在其它药物——包括paxlovid和单克隆抗体都不能用的情况下使用。
而且molnupiravir是在paxlovid上市前出来的,当时又是奥密克戎让多个单克隆抗体失效,可以说是一棵独苗。
现在阿兹夫定的遗传毒性风险比molnupiravir明确得多,药物疗效证据更少——molnupiravir好歹是做出了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的有效性的,又有其它抗病毒药与单克隆抗体,阿兹夫定是否应该被批值得商榷。
molnupiravir审核时FDA多位专家提出,一旦有其它更好的药物上市,需要考虑撤销molnupiravir。为什么现在中国有更好的药物,却还要上市阿兹夫定?
2.生殖毒性
阿兹夫定也存在明显的生殖毒性风险。这包括了大鼠与兔两种常用生殖毒性实验动物中多个结果阳性[1]。
比如大鼠生育毒性,这是在交配前后给大鼠给药。无论是给雌性还是雄性大鼠喂药,高剂量时都存在导致生育力下降的影响:
阿兹夫定对胚胎发育也有潜在风险。在大鼠妊娠早期给药,导致胚胎丢失率上升,5mg/kg的高剂量还影响了胚胎骨骼发育。
大鼠妊娠后期给药则对母体与子代均有毒性,子代影响包括了一些生殖系统与神经系统影响:
这些结果在兔子的胚胎发育毒性实验里也有重复,比如上述的生殖系统影响、胚胎存活降低以及胚胎骨骼发育问题等。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些生殖毒性实验中所用剂量都比较高。比如大鼠妊娠晚期对母体有毒性的最低剂量(NOAEL)是0.5mg/kg,致死剂量是5mg/kg。而阿兹夫定治疗新冠的人体剂量才5mg,按体重算比这些实验剂量小很多。
只不过动物与人体在代谢水平上有差异,比如实验用的大鼠、兔子,体型比人体小很多,代谢快很多。考虑药物剂量时需要做人体等效剂量的换算,比如大鼠的剂量乘上0.才是人体对应的剂量。这样算下来,大鼠妊娠晚期的最低有毒性剂量0.5mg/kg,对应人体是0.mg/kg,按标准体重60千克算,人体剂量是4.86毫克,比治疗新冠用的5毫克还低。喜提0安全空间。
就算是雄性大鼠生育毒性的NOAEL高一点,5mg/kg,换算下来对应60千克的人,也就48.1毫克,跟治疗新冠的剂量比,不到10倍的安全空间。如果哪个男生还瘦小些,只能说多保重了。
而且遗传毒性、生殖毒性都是比较特殊的毒性,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我们不能说到临床试验里去明确有没有,而是要考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风险,如果有,就要考虑这类风险是否可接受。因此,别说什么有毒性的剂量比较高,这两类毒性实验就是需要用较高的暴露剂量来探索潜在风险,参考molnupiravir[2]:
molnupiravir使用剂量mg,一天两次,但生殖毒性实验仍采用远超这一水平的剂量检测。需要注意的是molnupiravir一样观察到了类似的胚胎发育毒性,特别是骨骼发育影响,倒没有阿兹夫定观察到的对母体毒性。可就因为这些发现,molnupiravir是绝对排除在孕妇与未成年人中使用的,还被摁死在了其它治疗药物均不可用的情况下最末位选择。
阿兹夫定的限制在哪里?和遗传毒性一样,考虑到阿兹夫定的有效性还不如molnupiravir明确,这个药物是否该批需要考量。
3.关键是总体风险
阿兹夫定针对HIV治疗的技术评审报告中还提到了尚未完成致癌性实验,需要补充[1]。可考虑到这个药已经表现了非常明确的致突变性,也就是遗传毒性,致癌性的风险应该会是比较高的——癌变背后本身就是基因突变。
其实,更重要的是综合各项数据分析阿兹夫定的风险。
阿兹夫定(Azvudine,FNC)是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化学结构上是核苷类似物,与胞嘧啶类似(核酸序列ATCG中的C),另一个HIV常用药拉米夫定(Lamivudine,3TC)也是如此[3]:
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是HIV药物里的一大类,机理是结构与HIV逆转录复制基因组所需的原料——脱氧核糖核苷酸类似,与逆转录酶结合后可以阻断病毒复制。
但这样的机理必须